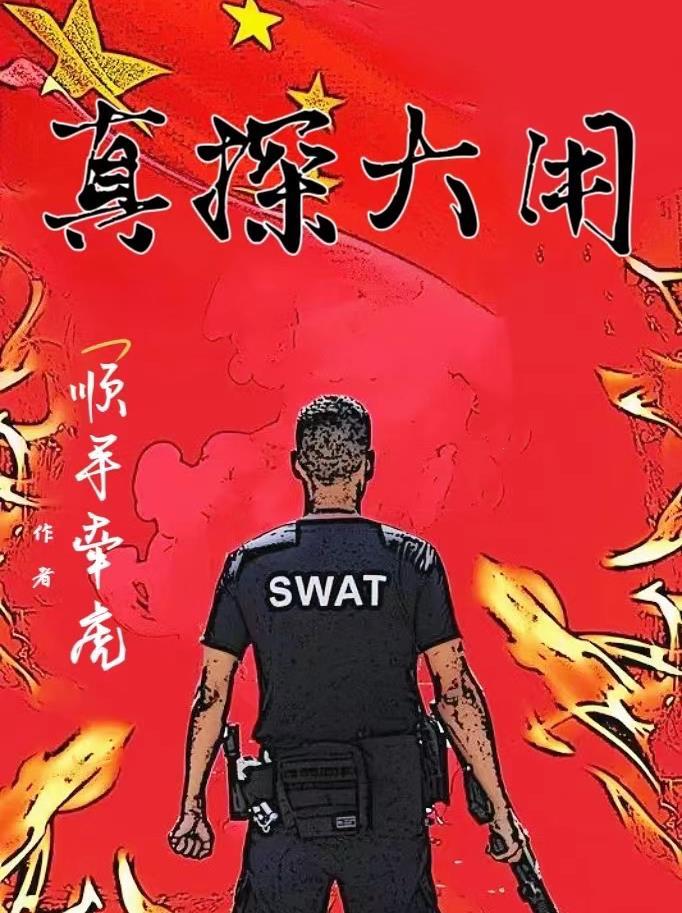帝国小说>万光:旧世界轶事 > 第12章 爱奴(第4页)
第12章 爱奴(第4页)
——我这么无能为力,你还会爱我吗?
……说什么傻话呢。
祂拉起祂的手,栽倒在床上,相隔许久,连同频率的呼吸和亲热都显得格外陌生。
你……你为什么来找我?
祂颤抖地哭起来,落下几滴泪,万用指尖划去,祂的脸又添一道水红色的沁痕。
你好笨呀,你去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你管我做什么,我都背叛你了,我都……祂还是哽咽着,只有这点我不想欺骗自己,那就是我只会更爱你这件事。
我也是一样的,光流。
祂只是想去吻祂,于是便这么做了,祂看起来像要死了般,裸露着触目惊心的骸骨。
秃鹫啃食曝尸荒野的尸体,也会食用到这个程度吗?
祂只是,用牙床的骨头去亲祂,用颧骨去蹭祂,从祂的额头到脚尖,往日里祂们无数次这样干过,去交流细细密密的爱意。
祂的血快把祂淹没了,祂让祂在祂的血里再度沉沦,研磨撕裂,委身于失重感中。
祂轻喘着,解开背后的丝带,长裙从祂腿间滑脱,祂被血泡着,薄薄的裙衫褶皱起来被丢弃了,祂说好冷!
祂无助地去找祂,抱着祂,祂完好却苍白的皮肤和祂的溃烂的缝在一起。
祂弯下身,蜷缩在祂怀中,连带着小腹内横冲直撞抗议的生命,祂才不要去管。
祂在祂怀里又抬头碰碰祂的脸颊,轻吻祂溃烂的黏腻的部分,祂想到伟大的诗篇和细菌的温床,体温升高,而后滋生的无数微生物,另一个小世界就在祂们的吻之间交流。
祂说你的血就快凝固了,凝结成一滴一滴坚硬的血珠,而祂被按压在固态的血泊中,祂就是祂琥珀里无动于衷安眠的昆虫。
祂知道呀,祂在一望无际的红色中想,祂埋在万火红色的丝中想,祂知道祂的脸祂的身躯比月亮倾泻下的冷光都要苍白了,祂比人类封存在坚冰中的尸体还要苍白,在冰层下,被挖掘,重见天日,他们推测说,这是适龄少女——祂比那还要憔悴,祂的睫毛都被冰冻。
祂不再美丽了,头的光泽黯淡,眼神也沉没进暗无天日的深海,祂心想祂和一张燃尽了的白纸已经没有分别。
可是万说你和以前的无数个日月一样美,这种假话……祂张张嘴,又只是哭。
你要挖出来我的心看看么?
快点,快看看呀,那样你就知道了,我只是一半的。
任何东西,只有一半也可以活着吧?
但是一半就是一半,只有,只有你的和我的贴在一起,那样才是一整个。
亲爱的,我曾经就是这样,我只是一半的去形单影只——那又是什么意思?
祂真想就这样牵起祂的手,除了无尽的夜色外再无其他,直到再次看见黎明的曙光,而那也是注定要和祂一起的,如果没有祂的话,去看一缕光又有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做的一切,只有唯一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祂们的声音在某刻重合又分离,那一瞬间祂们都在思考所谓永远的纯粹的无私的高尚的伟大的东西是什么,祂们抛出一个个词汇,又迅丢弃,直到根本没有言语足够资格去形容,祂们望向对方含情脉脉的目光相视而笑。
祂还是爱祂,祂根本不能不爱祂,祂将爱祂一直爱到祂死,这份爱太重太重,重到只有祂们合在一起时才能被对方理解,因此便可以让他人随意评判。
你知道我们是一体的吗?
一切都有消失不见的那一天,如你所见的潮汐,漫天的风沙,生活着的人类的窃窃私语,终有一日名为存在的概念会爆炸塌缩,变成一个空白坚硬的质点,再去萌生其他的。
那时祂就不需要思考了,就不需要去爱了,可惜祂的爱太沉重,祂怕把那质点也碾碎,祂怕那爱传不到哭泣的金光流的耳边。
到那时会如何,一切究竟会怎样呀,静谧的世界和心碎的人,祂不愿看见祂金色的丝悲哀地弥散在田间旧草中,或许还有溪流,冲刷掉一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前祂还有多少机会就只是单纯对金光流讲我有多爱你。
没关系吧?
只要心连在一起,就可以把要面对的东西遗忘吗?
就这样捏着手不要跑了,仅仅这样就好。等我再次睁开眼,你还会在我身边对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祂仍旧捏着祂颤抖的指尖,原来都是冰凉的,缠绵也不会有任何温度。
我不知道,祂翻身,抬头看着自己初来乍到时那灰蒙蒙分辨不出日月流转的可恨的天空,我不知道!
祂只当自己是爱奴是死囚,祂被永恒囚禁在祂的爱里,只尝了一滴蜜便心满意足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