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小说>熟仙艳录 > 第三章 日寡妇大车恋小马纯爱后宫母子熟女(第10页)
第三章 日寡妇大车恋小马纯爱后宫母子熟女(第10页)
地把整个头子具吞进嘴,香舌便施展不开,认那童眼儿里的残精味道涌上来,腥刺里带着些稚嫩青春,于那美妇讲,倒是一味琼浆玉液般的补品。
梁氏使双手把住少年鸡巴防他孟浪,若那东西整根入口,从此便要合嘴不上了,梁氏费力地从鼻孔里出了两口气,便提胸抬,奋力地吸了起来,直把那嫩阳中的残精尽数吸出,千万子孙浆没到孕宫,倒美了少妇口腹之欲。
梁氏见张洛止住哭,微眯起眼,便又故技重施,直吸得嘴唇都有些肿,却看那少年又蹙起眉,口中疼得直叫娘,梁氏见状便只好松口,捂住阳具问张洛到:
“洛儿,还痛吗?”
张洛点了点头到:“痛哩,人种袋袋都胀得疼哩。”
梁氏恍然大悟,原是这小童子开了蒙,攒下的童精一便要涌出,方才那一炮尚未排净童阳,积在童睾里,才憋得那小童儿直喊疼哩。
“洛儿莫怕,想是洛儿的童阳没排干净,憋在鸡巴里了,如此便好说,你既起性儿,只管和芳奴儿操逼就是,只是这番操娘但要尽兴,务把那鸡子卵子里的童精都排净了才是。”
梁氏翻过身,就把那羊尻肥臀对着张洛,妇人双手放在屄门上扒开软肉,那玉瓮淫穴早便红似肿,张洛方才泄出的阳精几乎要涌到牝眼儿口,如奶似蜜地扯着涎,垂着丝淌了出来,梁氏刚忙用手去承那滴出来的精羹,径直放在嘴边小口小口地舔吃了,又吮指舔掌仿佛意犹未尽,复又扒住屄,焦急地同张洛讲到:
“亲达达,你且进来,径直操干便是。”
张洛丹田如烧似炼,一股邪火轰地顺着脊梁窜入脑中,激得张洛顾不得许多,径直把那比驴马小不了几分的大肉屌“噗嗤”
一声揎进梁氏牝内。
“哎哟!”
梁氏此番只觉消受不得,母性交织着爱欲,便使梁氏顾不得许多,只要满足了张洛便好,梁氏咬得银牙咯吱咯乱响,口中却仍叫张洛使劲入去。
“哎呦,哎呦!亲达达!啊!啊!啊!……”
梁氏连那骚话也讲不出,只是母兽般嗷嗷叫唤,那阳具太过粗大,撑得一腔软肉都开胀起,那妇人被张洛肏得脑里昏,苦挨着被肏了三四百下后,更不知自己在何处了。
“骚奴,骚奴,俺干烂了你!”
张洛操得红了眼,当下扭腰挺胯,啪啪啪地干得梁氏尻股乱荡,梁氏屄内骚水让那大屌紧着研磨,泡得那肉屌上好似糊了层浆糊,带进带出间一都成了糊在美人屄口,好似一片片砌琼堆脂的奶油般黏腻。
“嗷,嗷,嗷!操呀,操呀!小活驴,把老娘干死吧!”
那美妇煎熬不住,玉手又抓又握,时而抓扯得供桌桌布都烂了,时而攥住粉拳锤鼓般锤得那供桌咚咚作响,张洛抽插四五百下仍无泄意,倒把那美妇干得翻眼吐舌,一听不清其口中在嚎得什么了。
“奴家不行了!嗷!”
梁氏倒吸一口冷气,轰地倒在供桌上晕死过去,张洛胯下那股憋胀之意越来越重,只好越来越快地对着那美妇可怜的牝眼儿不住日刺,极抽插间,张洛隐隐觉着胯下泛起一阵金光,那股憋胀之意也已到了顶点,便要从那马眼儿里喷薄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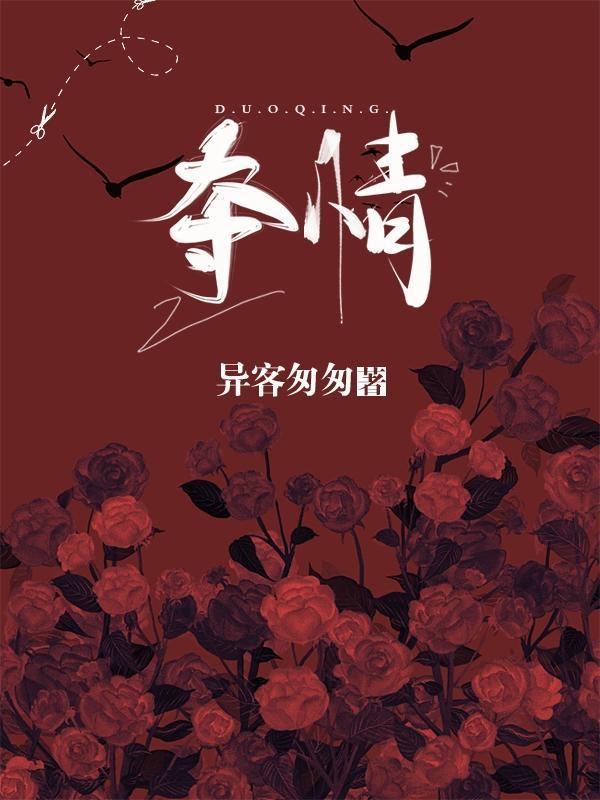

![小福星她五岁半[七零]](/img/486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