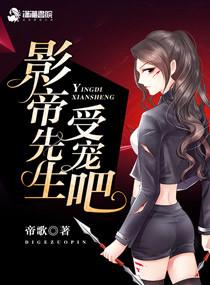帝国小说>大明:我靠系统卷死朱元璋 > 第29章 创伤(第2页)
第29章 创伤(第2页)
现在的大明朝堂与夏白所说的颇为相似,父皇只愿听取自己想听的话,对于其他不合心意的内容,直接命令百官不得提及。
敢说真话的人会被治罪。
长此以往,天下还有谁敢说实话?
即便是御史,现在也只敢弹劾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有些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弹劾,更像是在变着法子赞美父皇。
按照原本的计划,父皇本打算去乡间询问农夫的意见,再到应天府听听文人的看法,然而如今却不知道父皇是否还会继续这样做。
他也不敢贸然询问。
许久。
朱元璋收回视线,望着朱标,严肃地问:“老夫,你可觉得咱们确实做错了?”
“当年你母亲说我,你弟弟保儿也说我,还有那个姐夫,他们都提过类似的话。他们都是咱们自家的人,是亲人。若咱们没做错,为何他们会这般说咱们?”
“咱们究竟错在哪里?”
朱标拱了拱手,苦笑着说道:“父皇,孩儿不懂。”
“父皇让孩儿说。”
朱元璋瞪着眼睛。
朱标舔了舔嘴唇,“依孩儿看,母后的意图,孩儿不知。但孩儿以为,父皇的心意是好的,确实是为百姓着想。”
“父皇推行的定税制度,在孩儿眼里,确实是利民的好事。”
“按照定税制度,日后新开垦的土地不再增加赋税。如此一来,大明的耕地会越来越多,而人口也在增长,但赋税却不会相应提高。”
“这对百姓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朱元璋点点头。
这正是当初制定定税制度的初衷。
朝廷规定的田税额度固定后,大明的土地和人口只会不断增多,这样分摊到百姓身上的田税就会逐渐减少,百姓也会越来越富裕。
到时候朝廷如果缺钱,只需向百姓额外征收些口赋即可,基本不会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
这也是大明安定民生的长远之计。
朱标接着说:“父皇对官吏的监管非常严格,凡百姓发现官员有*行为,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直接将官员捉拿,押送到京城问罪。”
“这是大明政治清明的关键所在。”
朱元璋微微点头。
这确实是他的初衷。
然而推行了几年后,却没什么成效。至少这些年,他从未见过有百姓真的把官员绑到京城来。
以前他认为是政局清明的表现。
但现在。
他不再这样想了。
就算他已经颁布了相关法律,但官是官,民是民,百姓又怎么敢真正去告发官员呢?
朱标偷偷瞄了几眼朱元璋,见他并未动怒,便继续说道:“父皇的本意出发点都是好的。”